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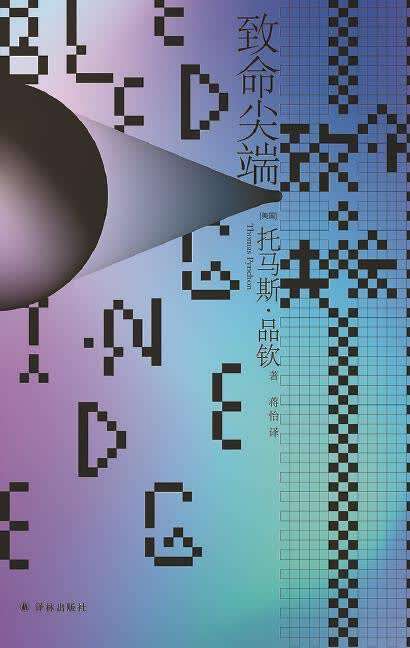
托馬斯·品欽《致命尖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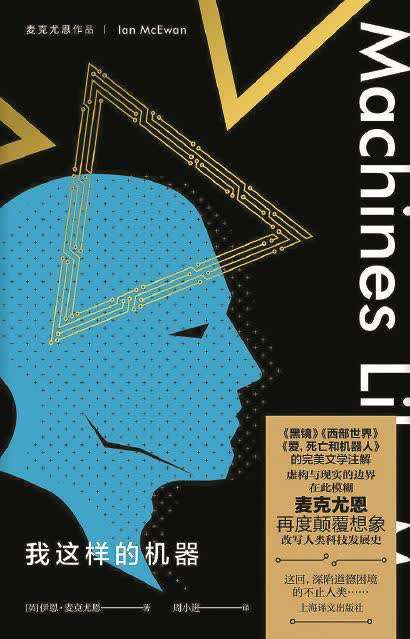
麥克尤恩《我這樣的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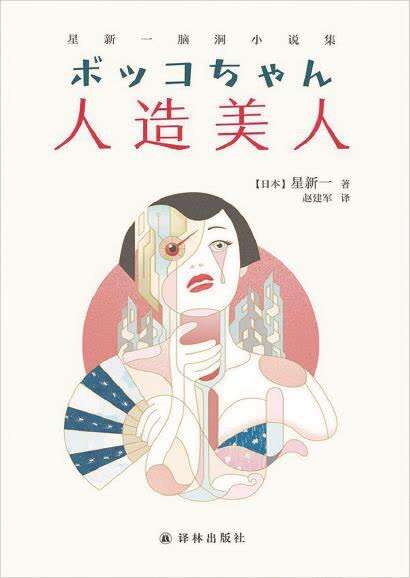
星新一《人造美人》

托卡爾丘克《世界墳墓中的安娜·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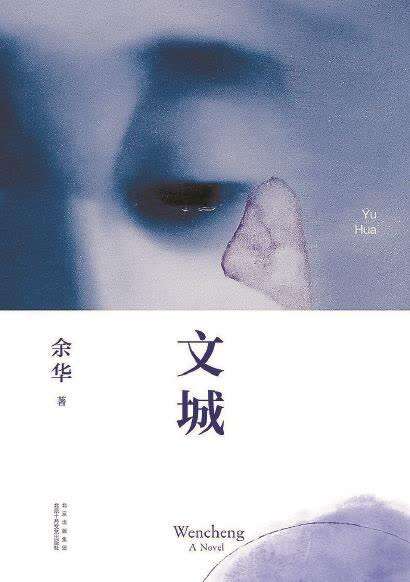
余華《文城》

東西《回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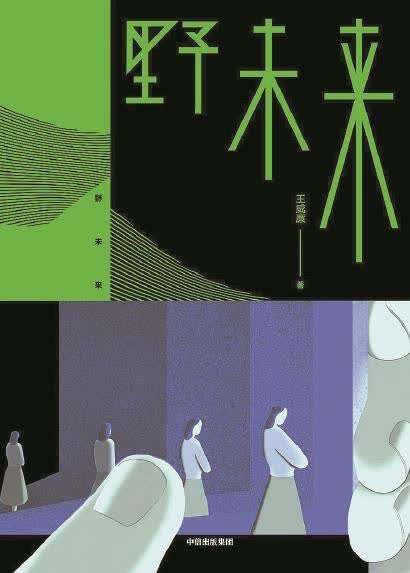
王威廉《野未來》

麥家《人生海海》
隨著網絡文學和科幻小說的興盛,近年來傳統文學創作者開始主動汲取類型文學敘事資源,出現了小說敘事上的文類融合現象。余華推出的長篇小說《文城》,就有評論家說這是一部“純文學爽文”,有網絡小說的敘事特征。青年作家王威廉出版的中短篇小說集《野未來》,也是一系列帶有科幻敘事特征的純文學作品。還有作家東西最新的長篇小說《回響》,也借用了偵探敘事來講述傳統的情感主題。阿乙最新小說集《騙子來到南方》,其中《嚴酷的事實》等篇開始回歸傳統,運用了寓言體和民間傳說的講述方式。相關作品還有不少,如邱華棟的歷史武俠小說集《十俠》,李宏偉的純文學科幻小說《引路人》,艾偉以懸疑筆法勘探隱秘人心的《過往》等等。這些原先從事純文學創作的作家,紛紛向科幻、懸疑等類型小說汲取表現手法,探尋著全新的文學風格。
不僅僅是傳統型的純文學向類型小說取經,此前類型敘事手法較為突出的作家和一些作者也轉型為相對傳統的純文學創作。麥家的長篇小說《人生海海》,不再有《暗算》《解密》等作品的諜戰、懸疑風格。一直以懸疑小說家著稱的蔡駿,其最新的《春夜》盡管還有懸案故事,但做新書推薦時,以“現實主義”“半自傳體”甚至城市文學等概念作為主要的評價話語,基本脫離了懸疑的話語。寫過諸多科幻小說的修新羽,也以一篇純文學作品《城北急救中》引人注目。早前曾投身網絡文學創作的李小糖罐,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后,開始以真名李敏銳在傳統文學期刊發表純文學作品。
致力于打破類型、進行風格轉型的作家還有很多,像黃驚濤、龐貝、王十月、黃金明、陳崇正等,多年前已開始創作科幻小說;須一瓜、田耳、雙雪濤等作家,他們的作品一直就有著清晰的懸疑敘事特征。網絡文學寫作領域,打破類型劃分、進行文類融合寫作更是一種常見的敘事現象。言情敘事幾乎遍及所有的網絡小說,偵探、仙俠、歷史、穿越,甚至盜墓都離不開愛情主題;傳統武俠小說的元素同樣也已經遍布各大網文創作類型。比如愛潛水的烏賊去年完成的《詭秘之主》,既是玄幻、魔幻,也是歷史、懸疑小說;憤怒的香蕉被改編成影視劇的《贅婿》,是穿越也是言情,是古裝也是商業類型。不斷地突破既有的類型劃分,糅合多種類型的通俗文學元素,這幾乎成了網文界最為便捷的創新途徑。
文學新浪潮:
強化現實感、改善可讀性和提升文學性
純文學向類型文學取經,類型小說作家向純文學靠近,以及網絡文學界常見的類型融合,這些現象說明今天文學創作已不再固守傳統的門戶之見,開始主動借鑒其他體裁、類型作品進行自我創新。這種“自我創新”,可聯系起近兩年文學界所探討的“小說革命”話題。
近年來王堯、楊慶祥等評論家、作家曾經探討如何理解和開展“小說革新”。傳統文學界之所以有進行自我革新的沖動,間接原因或許是傳統純文學的市場空間被網絡文學和新崛起的懸疑、科幻等類型小說所擠壓,但根本的緣由是傳統純文學作家自身尋求突破。
走出寫作的舒適區,直面全新的社會現實,表現新時代的精神,這是中國當代作家的創作使命,同時也是現代文學以來中國作家完成自我創新的不二法門。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史告訴我們,但凡作家固守傳統,不愿意去直視新時代新現實,文學就會“狹窄”,讀者會慢慢流失。
新世紀以來的文學創作,除網絡文學的迅速崛起之外,傳統文學也有著重要的發展軌跡:九十年代發展起來的那種個人化的寫作逐漸隱匿;綜合著個體精神表達與時代現實書寫的創作日益成為主導風格,但也因為這種寫作注重現實的深度表達和內在精神層面的隱微流露,普通讀者理解起來有難度,所以影響力沒有破圈;寫實感強烈的文學創作、紀實性特征突出的非虛構寫作逐漸受到重視,這類作品成為一些作家擺脫寫作困境的出口;作家借鑒懸疑、科幻等類型敘事元素,以及汲取中國傳統通俗文學資源的現象越來越多。這幾種現象,特別是后兩種是作家們進行自我革新的探索表現,這種自我革新背后當然有著整個文學界的創新思考。非虛構、類型敘事、通俗風格,這些于新世紀初屬于小溪流一般的探索實踐,持續多年之后成了當前文學界的創作趨勢。
當然,并不是說非虛構和類型敘事將取代純文學創作,而是說整個小說界呈現了一個敘事融合、風格轉型的階段。這不是誰取代誰,而是每一個類型的寫作都在加速變革,而且是打破隔閡、相互借鑒式的綜合性改變。傳統純文學創作將借鑒其他類型創作的敘事資源,更強調現實感和可讀性,更進入時代,深入生活現場,同時也努力獲得更廣泛的讀者。非虛構、類型小說也會更進一步地重視文學性,非虛構寫作不會是過去的報告文學,類型文學也不會是以往純粹娛樂的通俗故事。
網絡文學,也將在全方位的網絡文化建設背景下,更主動更深入地向傳統的經典文學學習,不斷突破類型敘事模式的同時也注重語言的打磨。這些新變,意味著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這不是以往很多人認為的不同類型寫作將壁壘分明、各自獨立、不相往來的狀態,而是各種類型寫作相互借鑒、不斷突破邊界的“文類共融”時代。
創作上的類型融合探索,理論上的小說革新探討,如此兩相合力,構成了一個不可忽視的文學新浪潮。這個浪潮以小說創作的類型融合為主要創新方式,以強化現實感、改善可讀性和提升文學性為直接的融合目標。余華《文城》被評為“純文學爽文”,原因也在于小說中的人物形象過于清晰,尤其小說主人公有“打怪升級”的神力,“爽感”無限。但是小說最終并沒有順從于網絡文學的英雄模式,主人公在讀者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就死了,這不會是網絡小說讀者愿意看到的“故障”。阿乙用《嚴酷的事實》和《憤怒》等寓言敘事來探索新的文學風格,目的是“繼承中國小說的故事傳統,讓小說重新回歸流暢易讀”,也是在完成現實觀照的同時,強調小說可讀性的重要。
融合敘事:
科幻敘事、現實主義寫作與越界能力
在當前的類型融合敘事中,最流行、最值得討論的或許是科幻敘事與現實主義寫作的融合。文學界已出現未來現實主義、科技現實主義、科幻未來主義以及“純文學科幻”等表述,這些概念既來自傳統的純文學寫作者,也來自科幻小說家。他們都想借科幻敘事展開想象,用一個更具未來感的故事揭示當前世界的問題。像王威廉《野未來》里的青年,他們通過科幻作品所想象的未來,會與自己作為個人的未來命運有關系嗎?用科幻虛構出宏大、浪漫的未來,比照出現實世界中迷茫的個體,既有現實批評,也有技術反思。科幻作家晝溫的《偷走人生的少女》就整體而言是傳統的寫實風格,作家很樸實地講著未來的故事,想象了人可以通過高科技設備復制他人的頭腦思維時,我們將面臨怎樣的道德困境。還有更多的作家,都是借未來生活的可能性來揭示當前現實的命題,或用反思科技的故事直面一些永恒的人性問題。
對于科幻敘事,楊慶祥曾有一個判斷:“不能將科幻文學視作一種簡單的類型文學,而應該視作為一種‘普遍的體裁’。正如小說曾經肩負了各種問題的探求而成為普遍的體裁一樣,在當下的語境中,科幻文學因為其本身的‘越界性’使得其最有可能變成綜合性的文本。”把科幻文學視作一種“普遍的體裁”,對于早期作為科普宣傳文本的科幻文學而言可能不會成立,但對于今天科幻敘事和純文學相互融合趨勢下的科幻文學而言,作為未來文學的“普遍體裁”完全有可能。
科幻敘事有著超強的越界能力,其文本綜合能力將越來越突出。這不僅是當前中國小說創作的新現象。最新譯介的外國小說中,像麥克尤恩的《我這樣的機器》、托馬斯·品欽的《致命尖端》、星新一的《人造美人》以及諾獎獲得者石黑一雄的《克拉拉與太陽》、托卡爾丘克的《世界墳墓中的安娜·尹》等等,這些小說也在用科幻的故事探索著未來人性的變異可能。這些當代重要作家最新的創作動態,將作為一種世界文學新趨勢的外部力量,影響著中國作家的類型融合選擇。
科幻敘事對當前中國小說界的影響,可以聯系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當年馬原、余華、格非、蘇童等人的先鋒寫作,其先鋒性往往體現在敘事結構、小說技巧方面的實驗,而這些技巧有些也源自偵探懸疑類小說。八十年代先鋒小說對于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而言,無論是小說語言還是敘事方式,其影響都是深刻而長久的。今天,傳統寫作與科幻文學以及更多類型小說之間的相互融合,所帶來的小說創新,讓我們期待著“文學共融”時代的“融合”之“融”,將轉化為“繁榮”之“榮”。
(作者為暨南大學文學院講師)
關于我們? 合作推廣? 聯系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互聯網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